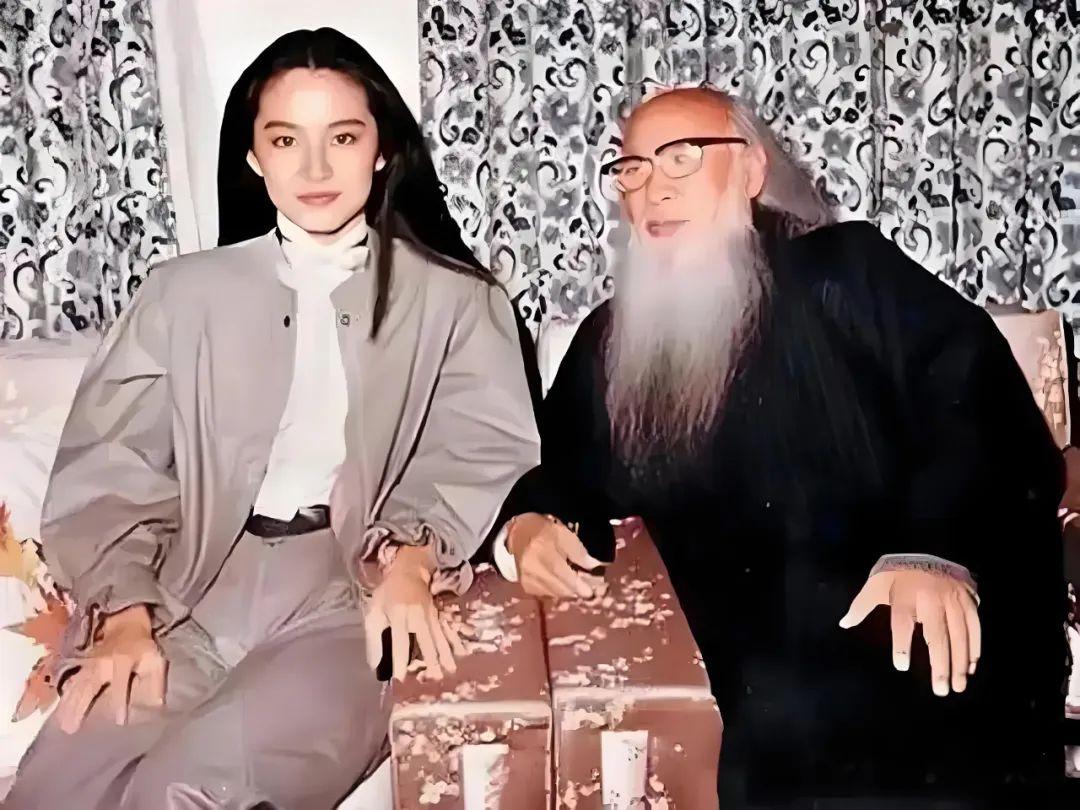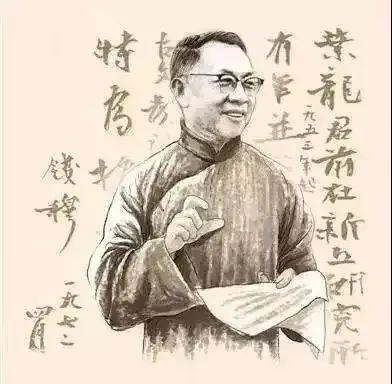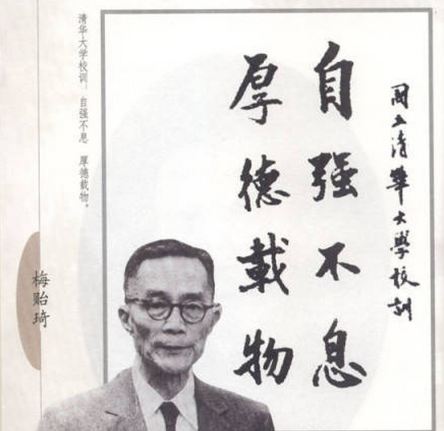"你会有这种感觉吗?"她看着我,神情有些迟疑,问道。 她是我的一位学生,一位室内设计师。她计划在三十岁那年放下手头的工作,来法国继续深造。上周六,她谈起在油管上关注的一对夫妻——一个是台湾厨师,一个是英国人——他们在法国生活了十年,最终决定搬回台湾。原因很简单:他们觉得自己在法国,始终是"异乡人"。
我愣了一下。这个问题,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。它像是被塞进了记忆深处的抽屉,一直没再翻找过。我摇了摇头,只说了一句:"你不能太敏感。" 这句话,是我对她说的,也是过去这七八年里,我反复对自己说的。
归属感,曾经是我执念的幻影
"归属感"这个词,对我来说,并不陌生。
还记得来法国的第一年,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急切的渴望,想要找到它——归属感。那时候,我以为它意味着一个"社会身份"——要讲流利的法语,像法国人那样谈笑风生;要进入法国人的职场圈子,要融入他们的社交网络。仿佛只有做到这些,才能证明自己"不是一个外人"。
可是,现实并非如此。
九年前的日记里,我写过这样一句话:"这一年过得很快,仿佛转瞬即逝。每个人回头看时,都会觉得时间飞逝,但陷入其中时,却像掉进了泥潭,怎么也过不去这道坎。"
我知道,那道"坎"是什么——就是我以为的"归属感"。 那时候的我,除了上蓝带的课程,其余时间几乎都花在练习法语。
我在商店、学校里,尽力只说法语,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,店员、学校的 chef 还是习惯性地用英语回应我。我想结交法国朋友,可是每天陪伴在我身边的,却是一个乌克兰男孩。 直到遇见了我现在的先生——一个来自法国西部小城、来巴黎学哲学的男孩——我才短暂地以为,也许自己终于可以融入法国了?
可是,现实又一次让我失望。
我依然记得第一次去见他朋友们的场景。那天晚上,我刚下课,赶地铁时遇到线路故障,心里一度想找个理由推掉。但还是咬牙坐上了人生中第一辆巴黎出租车。那次出租车花掉的钱,几乎是我几天的生活费。 我记得那个二十区的公寓,温暖又宽敞。朋友们起身迎接我,微笑着贴面礼。我还不太适应这种"过分亲密"的方式,只能僵硬地回应。他们喝了很多酒,聊天的语速像鱼儿在水里快速游过。我听不懂笑点,只能偶尔跟着笑,偷偷看向男友。他朝我眨了眨眼,举起酒杯,仿佛在说:"放轻松。" 可我并不轻松。我只是觉得,自己格格不入。
到底什么是"归属感"?
我妈妈总是劝我们回国。她总说:"不能总在外面漂泊。" 在她的观念里,漂泊意味着不安定、不踏实。她总觉得,人必须"扎根",像一棵树,要把根系深深地扎入土壤。而这片土壤,理所应当是你的家乡,是你出生长大的地方,是"落叶归根"的归宿。
曾经,我也以为归属感就像一块必须耕种的土地——你得努力去融入、去被接纳,才能算是"真正扎下根来"。
刚到法国的那几年,我试着融入法国人的社交圈,去参加他们的派对、聚餐,我想证明自己也是"他们中的一员",想融入他们的世界。可是,无论多么努力,那层看不见的隔膜依然存在。那是一种微妙的、无声的边缘感——不是谁明确拒绝你,而是他们在分享一个只有他们才懂的世界,而你始终站在外面。
我常常在脑海里反复问自己:是不是我的性格有问题?是不是我太敏感了?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幽默?是不是我永远不够好? 但这种感受,并非绝对和无法化解。
当我看到餐饮行业中有很多外国人,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、说着不同的语言,其实,我们彼此也并没有那么在意对方是不是"外国人",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故事,各自的起点。
我记得很清楚,在一家法餐厅工作时,一个来自孟加拉国的洗碗工,每到祷告的时间,就会铺开一块深蓝色的围裙,跪在自己的工作区域里,面朝特定的方向,安静地祷告。而我们只是从他身边经过,没有人投来特别的目光,也没有人表现出异样的情绪,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。
归属感,原来是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
我开始明白:归属感并不需要通过"变得一样"来获得。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有着属于自己的背景、文化和故事。 工作的环境也不需要你放弃自己去迎合别人。 慢慢地,我学会放下"必须融入"的执念,开始回归到一种更轻松的状态: 我就是我,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生活。这种感觉就像安全感,最终就是一种内心的状态,它或许本来就不是别人能给的。
只要我还生活在远离自己故土的地方,只要我还是黄皮肤黑头发,可能注定会在某一种场合,某一个时间,被某一些人贴上"外国人"的标签。但最重要的是,自己是否会被这种"标签"所困扰,想清楚自己为什么选择生活在异乡。
我们常常以为,只有"被接纳",只有"被喜欢",只有"和他们一样",才算是"融入"。但也许,真正的归属感,不是关于"他们",而是关于我自己——能否在不被看见时,依然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完整的?能否在被区别对待时,仍然觉得自己值得被珍惜?能否在站在"边上"的时候,依然自洽而安然,而不是强求自己进入别人的圈子? 我不再期待自己一定要"像他们一样"。
我可能不能在这里长成一棵大树,但希望自己即使不在原生的土地上,也能在别处生根发芽,用自己的方式,缓慢而坚定地生长。